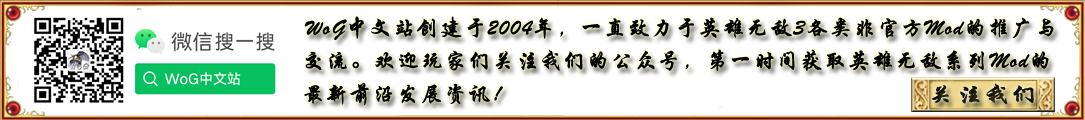|
|
我如果写很多字,那就是无字,我不知道有人会看出什么,因为我写完就破晓,然后我睡了,忘了。
我是一名削肾客,在竹马殿以削肾为生。
永泰十五年,天下饥荒, 我便投入我师父门下,师父摸着我的手说我手骨精奇,是天生的削肾客。
我跟随他,七年练气,七年练眼,剩下的三年练拔刀。师父说,你要一眼望去,透过重重皮相,便能看尽腰子的形状和走向。
神定再手动,出手后就不能再有犹豫, 他们虽然削肾,但也是人命,伤了人命终归有违天道。
这饥荒一直持续到永泰三十四年,饥荒之后就是盛世,削肾的人便慢慢多了起来,他们多半穷苦,但更多的是年轻为了爱情。
师父每次削肾都会沐浴更衣,着一身白衣,白衣如雪。师父还会置一个香炉,焚一柱清香,香完肾落,白衣不落一点血迹。
他每次出手我都会在旁边观看,他的出刀很快,往往我还没看清楚,肾就落下了,被他一手接住。我问师父,明明只需要一刀, 为什么还要点一炷香的时间?
他说,身体发肤,承与天地受之父母,这一注清香是还给天道人伦。
永泰三十七年,那年师父四十岁,镇头的王麻子来削肾,他需要一笔钱给母亲治病。师父如往常般沐浴更衣,他的出刀在我眼里慢慢变得迟缓起来,清香燃尽,师父的衣角多了一丝血迹。
师父没有收王麻子的钱,像瞬间老了许多般。
那天子时,周围漆黑不辨。师父把我叫进了内厅,那里檀香冉冉,层层牌位,每个牌子前都有一个盆子,他说供奉的都是历代削肾客。
师父指着最近的牌位说,这是我师父,牛犊子。
师父又说,你还不知道为师的师承名号吧,我师承牛犊子,名号狗肾子。
我想起师父白衣胜雪,出刀飘逸,实在想不透这名号。
师父说,削肾客夺天地造化,极伤阴德,因此取名都是落入五畜道,你师承我,以后便叫猪腰子。
师父不待我应承,又说道,名号已定,你只要赢了我手中的刀,便是真正的削肾客了。
其实我早就料到了会是如此,我七年练气,七年练眼,三年拔刀,没想到第一次居然是要面对是自己最尊敬的人。
室内灯火昏暗,我和师父擦身一刀而过,烛火暗了一下又猛地拔亮。我手中已经多了一个温暖的腰子。师父立在门口,大口的喘气。他的身影佝偻。仿佛不堪重负。
很久他才说,很好,很好,从今天起你就是真的削肾客,帮我立个牌位,盆子放我的腰子。列祖列宗的规矩,不能坏在我手里,他语气冰冷,都没看他的肾,视腰子如无物。
师父推开了门,慢慢的走出去,一步一步,师父忽然停了下来,对我说,我一生未娶,无可挂念,倒是你,命里多劫数。削肾客最大的敌人就是孤独。
师父一步一步,缓缓步出我的生命,那年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我按他的交代,把他的牌位他的肾供奉起来,早晚清香。
我想他是离开了,还是离开了,这是传承的力量,冰冷的超脱俗世间的感情。
他走后,我甚至觉得无所寄托。
削肾客多半感情凉薄。世态炎凉,淡薄才能活得久些,我见惯悲喜,甚至轰轰烈烈到割肾相许的爱情。
永泰三十八年,我开门削肾,我什么都学着师父,唯独喜欢穿一身黑衣,犹如一滴浓墨涂在这灰霾的尘世里。
我成了最年轻的削肾客,焚一柱清香,香尽肾落,一切都是那么的循规蹈矩,我知道我还能更快,但是这一炷香是要还给天地人伦,我还知道我的衣服上不会有一丝血迹。
我削的第一个肾是小王的,他的未婚妻想要一个爱疯五,那时我削一个肾收八文,小王在酒馆跑堂,一天三文,一个爱疯五要三两银子。
一个肾能买四两。他说,剩下的一两银子还能买点东西做聘礼。
师父还在的时候我就见惯了这样的爱情,我听的面无表情,只是告诫他,剩下的一两银子最好留些买点补品,削肾很伤元气。
他笑笑,说他还年轻,也问过别人,少一个肾不会死,只有一个肾都没有了才会肾衰竭,他说他还扛得起。
这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在我听来如同儿戏,我笑了笑,没理由拒绝。
我没收他钱,我告诉他,这是我第一笔生意。他面色惊讶,不敢相信我的手法如此纯熟,他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我说,你现在感觉不到,以后会的,失去的,不是你能弥补的。
小王摇了摇头,呵呵笑道,腼腆的说,我就想给她买个爱疯五,她喜欢,我就喜欢,这就是爱情。
小王又问我,你多大,喜欢过人没?
我算算,七年七年加三年,我六岁拜入师父,我说我二十三岁。
小王又惊讶,说道,你比我小,你没经历过,不会懂的。
小王辞别我回去,彻夜排队去买爱疯五。
红尘爱恨,哪里是论年纪?
你痴长几岁,怎知我不懂情?
师父告诉过我,削肾的时候最好不好说太多的话,免得入局。
我第二天便遇到了小王,在他跑堂的酒馆,我点了一壶老酒,他送了我一碟腌菜,回头对掌柜说,记他账上,从工钱里扣。
他的面色不好,见我却还是乐呵呵的笑,他抽空坐在我旁边,描述她的未婚妻见到爱疯五时喜悦的表情,手舞足蹈,喜悦逾于言表。
我自顾自的温酒,不理他,他依然自顾自的描述。
我喜欢喝老酒,辛辣,后劲足,伤喉却最能暖人心。我喝完一壶,他依然还在描述,苍白的脸上泛现红晕。
最后见到小王,是在法场上,他杀了他的未婚妻。
我如命运般冷眼旁观,路人的言语,亲人的唏嘘。他看见我,我用眼神询问,有不有后悔?
他别过脸去,避开了我。
少年的倔强一直撑到刀起,人头落地。
他自死没有看我一眼,就如同那天在酒馆,我自顾自的喝酒,没回他一句。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他眼里的爱情,那晚我在师父的牌位前坐了很久。
如果我只是一个如我师父一般的削肾客,接过他的钱,替他取一个肾,不问缘由,只管一刀。
那故事会不会是另外一番光景。
我遇见第二个人是青梅。
永泰四十年,我遇见青梅,还在在小王原来的酒馆里,我坐原来的位置,只是跑堂的伙计换成了别人,我喝着老酒,就着风,没有咸菜压舌。
青梅送了一碟蚕豆给我,坐到我的旁边,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也听到了她银铃般的声音,她说,你是个有谜的人,我送给你蚕豆,省得你喝闷酒。
她还告诉我她叫青梅。
我不知道怎么搭理,自顾自的喝酒,一壶尽,我便起身就走。
第二晚,我喝酒的时候,青梅依旧送一碟蚕豆,她依然坐在我身边,问我,你怎么总是一身黑衣啊,是不是没洗过,还是没得换。现在的公子哥都穿的花花绿绿,你是不是江湖人啊,这么神秘。
我没想搭理她,一壶老酒,如往常一般回我的店铺。
自此我每天都会遇见她,她送一碟蚕豆,总爱问我一些问题,她问我我是刀客还是杀手。为什么不说话? 这么闷闷坏人怎么办?是不是哑巴。
我停下来,想了想,摇了摇头,温着我的老酒。
不说话,便会少很多纷争,对江湖对削肾客来说,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慢慢的很少接到生意,我怕我手抖,衣衫上染上血迹,虽然看不到,但是会染到我心里。
再遇到青梅便是立冬,她送一碟蚕豆,我要了一壶老酒。她依旧问我很多问题,见我不理,便从身后掏出一个爱疯五。放在桌子上切水果。
她的手指纤细,很白,甚至能看到手背上淡淡的青筋。
她切的很快,每一刀都出的很准,拿了很高的分。
我便想起了小王,我忍不住问她,未婚夫送的?
她见我说话,笑笑,瞬间眼色暗下去,撇撇嘴说,才不是呢,我自己买的,自己赚钱买的。
她把自己两字咬的极重。
老酒杀喉,但暖人心。
立冬过后便是小雪,那天真的下雪。不大,刚刚侵满大地。我在宜春院前遇到了青梅,她不再青涩,浓妆艳抹。
我听见几个男人叫他杏红,她也看到了我,眼神里有一点慌张和闪躲。
我想,从青梅到红杏,这要走很多个四季。
我知道她是做什么的了,也知道她的爱疯五怎么得来,我没有半点嫌弃。
红尘这么大,总会容的几个人的风尘。
再见青梅,我吃了她的蚕豆,邀她一起喝酒,她久在风尘却从没有喝过这么老的酒,一直叫辣。
她说,我年纪这么轻,怎么总爱喝老酒,不怕伤喉?
我说,能暖人心,我和她碰杯,她别嘴,一口焖下。
然后很久我便没有见过她了,我要了老酒,却没人送一碟蚕豆。
那个酒馆我去了好多次,喝了好多壶酒,却都没遇见她,我一直想或者她离开了,风尘只是路途,不是归宿。
会有一个人替她赎身,给她一分平淡的爱情,不需要削肾的爱情。
我不想接生意了,拒绝了很多削肾的人,甚至他们加到了很高的筹码,我关了店铺,打算离开。
我敌不过孤独。
我离开的时候,是大寒,遇到了青梅,她已经是妇人的装扮。
我轻轻的说,我,我要离开竹马殿了,我欠你一碟蚕豆,怎么还你?
她直勾勾的看着我,一字一句的对我说,
愿得一人肾,换取爱疯五。
岁岁和君共,生死与君同。
我记得这首情诗,小王曾经念过,我叹了口气,我说,一定要这样证明?你不是有爱疯了么
她低下头,手指紧紧地绞着轻轻说,那是尼采。
她顿了顿,说,如果可以,我更想看你的心。
我掏出刀,我好久没用过的刀,我说给你吧,我也想知道我的刀有多快,以后多用正版。
这一次,我没有焚香,也没来得及沐浴更衣。
原来,削肾真的一点都不疼,只要你的刀够快。
大寒的黄昏,我离开了竹马殿。我挥一挥手,夕阳透过我的手掌洒下斑驳的倒影。
我没回头,留给她一个腰子,也没猜她的表情。
我说我是一个削肾客,生性薄凉,本该如此。
永泰四十一年,我越来越虚弱。我才知道从来就没有赢过师父。
我其实挺想像师父一样做一个纯粹的削肾客,那怕孤独,哪怕只有一个腰子,却能终老。
[ 本帖最后由 姓朱名德正 于 2013-6-9 17:32 编辑 ] |
|





 透视大地
透视大地 透视大气
透视大气



 发表于 2013-6-9 13:12:36
发表于 2013-6-9 13:12:36
 祈祷术
祈祷术 圣灵佐佑
圣灵佐佑 悲痛欲绝
悲痛欲绝 欢欣鼓舞
欢欣鼓舞 变色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3-6-9 13:18:11
发表于 2013-6-9 13:18:11









 楼主
楼主
 杰拉德这代也老了。。。。。
杰拉德这代也老了。。。。。









 发表于 2013-7-31 14:07:47
发表于 2013-7-31 14: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