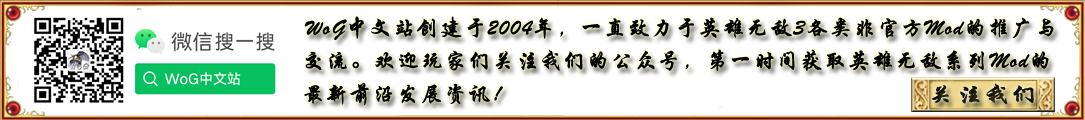杀猪
杀猪东北的寒冷总是来得那么早,不能江南的秋老虎夹着尾巴逃走,嫩江的雪便随着西伯利亚的寒流迫不及待地给大地床上一身孝服。农村的庄稼人虽不懂得风花雪月,但也颇知道“瑞雪昭丰年”的道理,老苍头披上厚厚的花里子棉袄,叼上儿子从城里买来的“带把的”烟卷,乐呵呵望着满天大雪,喜滋滋憧憬着明天开春时苞米的收成。倏忽之间,满天的鹅毛变成了张张印有伟人的票子,慢条斯理地落在田间地头。老苍伸手去抓,那票子竟实实在在地握在手中,沾满汗水和油渍,笑嘻嘻地等着他去清点。
美梦正延续间,一声闷声闷气的哼哼让老刘头手中的票子化成了闪着冰晶的冰水混合物。那是圈里的猪。
白色的大地在猪儿看来不似庄稼人眼中那么美丽,说是孝服可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从主人家的脸上和陆续回来的打工者们可以看出年根将至,猪的大限也将至了。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大概是人类替猪类表达出的一种心声吧,猪此时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历史含义,回首往事,恍如昨日,万千感慨化为食欲,不尽又是大吃一顿。
刘娘扶着栏杆欣赏猪的吃相,眼中看到的好像是她三个儿子早年在炕头上争抢窝头的情景。如今儿子都进城去了,这份颓然的母爱便漫无目的地发泄在猪的身上。刘娘经常故意多放半勺水,把苞米茬子熬的稀烂稀烂的,老头子吃不多少便撑饱了,每每都能剩下大半碗,那可是猪最好的美餐了。猪也从未无视刘娘的爱,鼓足干劲,闷头疯长,直到膘肥体壮行动困难不堪自重也毫不懈怠。邻居们看到刘娘的爱猪,无不夸老刘家的把势好,娘们会过日子,颇增了许多面子。
“我去二拐那一趟,明儿后晌动手。”老刘头恶狠狠地掐灭烟头,拍拍手中化为冰晶的“票子”。
猪愣了一下,默默到“他们终于要下手了。”继续疯吃。
“后晌?”刘娘给猪槽里加了一把料。
“大柱、二柱是要回来的,小三八成也能回。杀猪,过年。”
刘娘默默看着大块朵颐的猪,把碗里的剩饭全倒进猪槽,呆呆望着自己的宠物,不再说话。
老刘头推开二拐家的门,“在家?”
“来了。”二拐坐在炕上没有动弹,炕桌上铺满各种长短刀具,个个放着寒光,件件夺人二目。一件老辈留下的羊皮袄搭身上,斜眼瞥了一样老刘头。很有些“我坐在城楼把景观”的劲头。
“吃了?”老刘头掏出烟卷抵过去。
“吃了。”二拐接过烟卷,一脸不屑地看看牌子,顺手夹在耳朵上。
“明儿后晌有空?”
“后晌……”二拐瞥着嘴抬起头凝视房梁半晌,“不好说……敖三家有两口……晌午能不能整完……不好说。”二拐一手摆弄着刀具,一手抚摸着下巴上稀稀拉拉的胡子。俨然在规划心中的“长远计划”。
“知道你忙,这不跟你商量嘛。”
“都是乡里乡亲的,是谁家不去谁家……咂……”二拐闭紧双唇,又猛地打开,让气流快速在口腔中回旋一圈,用吸力抽出牙缝间的污垢,发出“咂”的一声感叹,做为难态。
“你大侄子过年回家,到时上家喝酒去。”老刘头是谈判桌上的老手,总是能抓住对方的弱点。
“成,杀完敖三家,立马杀你家。”二拐的承诺的是值千金的,村里唯一的屠户不仅业务水平高,屠德屠风也是有口皆碑的。
“好好。”老刘头唱了个诺,又谈了些去年从儿子那听来的城里新闻,便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火堂里的火苗蹭蹭地串出锅沿儿,陪着噼啪的断裂声烘得屋里暖洋洋的,硬生生地挡住刺骨的严寒,营造出一团温馨。可刘娘却不愿在这样人造的温馨中,她宁可陪着即将归西的猪身边。她从未听说过外国有个叫弗洛伊德的,更不知道什么高深的心理学理论,但她用在这头猪身上的意识转移理论却比任何一个专家都要如火醇青。
“要过年了,你怕是躲不过了。”猪嚼着美味的豆子,哼哼两声。“大柱、二柱回来是要吃肉的,小三更是没肉不行……”猪对此并不关心,在谁的消化道里变成粪便已经它身后之事了。“唉……”刘娘看着猪儿大义凛然的劲,不禁有几分酸楚,想起了几句为它准备的悼词:“猪呀猪呀你别怪,猪羊本是一道菜……”反复咏颂了几遍之后,心理好受了一点,老刘头的呐喊也随之而来:“水她妈都开了,整啥呢!”
即使是混沌的阳光,也能使皑皑白雪映出夺目的光芒,北方的冬天虽然漫长而寒冷,可这一片闪亮的白色已经足以让猫冬的老少爷们享用的了。就在这片白光闪烁中,二拐披着羊皮袄远远走来,腰间佩戴的刀具随着吱吱呀呀的脚步声奏出迎接新年乐曲。后面跟着几个打下手的伙计,远处是一群唧唧喳喳的孩子,手里拿着长短树枝木棍,比划吆喝着。
二拐杀完了敖三家的并不十分过瘾,打下手的新国新华哥俩笨手笨脚,洗手水冰凉刺骨,递上的烟卷也是不“带把”的,最可气的是不懂规矩的老敖家竟然割了一块肋扇做为报酬。这一切让二拐很不开心,自己的专业技能没有得到认可。同时让他对刘家的猪充满了希望,毕竟这家人是懂规矩的。
“来了。”老刘头顾不上穿棉袄,手捧着“带把”的烟卷迎上前去。
“来了。”二拐毫不客气地接过烟卷,看看牌子,叼在嘴上,让老刘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问:“备好了?”
“早就备下了。”老刘头散开身子指着院当中的条凳和脸盆说。
“嗯。”二拐哼了一声,打开猪圈,评点起刘家的猪来。“要说还是你家的状,就这怎么也能出200斤,最少得有四指油。”
“唉,瞎养,瞎养的。”得到评论家的赏识让老刘头很是高兴,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得到了面子上的肯定。
“来了。”刘娘在得到肯定之后也跑到院子里,一边给老刘头披上棉袄一边和评论家打招呼。
评定会结束之后,二拐并不急于上手,大步退出猪圈,挥一挥手,让新国新华打头阵。“绑了。”
“嗯呐。”二人答应一声,手持绳索冲入猪圈。二拐则和主人家蹲在当院叼着烟卷看徒弟们的实习。
猪是敏感的,甫一看见二拐的出现就知道刽子手到了,等到鹰犬们侵入领地便打起了游击战。鹰犬往东,它便往西,鹰犬进攻,它便撤退,鹰犬围剿,它便突围,鹰犬休息,它便出击。好是折腾了一阵子,那绳索还是没占着半点猪毛。
二拐好似故意让两个后生出丑一般,也不加指点,只等二人忙活累了在显出手艺来。就像小说里为了抬高某人故意丑化另一位配角似的,新国新华哥俩无形中成了二拐的华生医生。
“败家玩意,甭折腾了。”二拐丢下烟头,呼地站起,大师终于要出手了。
只见大师双肩一抖,羊皮袄顺势落在老刘头手中,腰间明晃晃的长短家伙顿时在黑土白雪掩映下闪现出来。三两步跨进猪圈,对着猪微微一笑,展露出香港电影里的顶级杀手面对最后敌人时的自信。
猪也知道寿数已尽,眼前这位是万万躲不过的,索性低头顺眉,做投降状。
二拐见猪递了降书顺表,还不罢休,用手一挥,让猪又跑了起来。不跑的猪谁都能抓,显不出大师的手艺来。跑了两圈,围观群众也都知道这猪难抓了,徒弟们也都等急了看师父的手艺了。二拐一个蹁腿,猪猛地来个180度横滚翻,斜下里摔在地上。大师就势弯起前腿,顶那厮面门,弓起后腿,稳住下盘,三两下便将天蓬元帅治的服服帖帖。
没等伏法的猪含冤,二拐双手拎起猪爪,交叉胸前,大手向徒弟一摊。“绳。”新国递上绳索,二拐左绕三下,右打两转,双手上下翻飞,十指行云流水,没等观众们看清所以然,一个“猪蹄扣”早将八戒捆的结结实实。这“猪蹄扣”是屠夫们的专业术语,被绑住的猪越是挣扎扣越是紧,也算是制式手铐发面前最使用的一种束缚工具了吧。
捆了猪,二拐接过刘老头递上的第二根烟卷点上。以胜利者的姿态俯瞰一阵,招呼鹰犬,“抬。”
“嗯呐。”哥俩答应一声,插上木棍,抬猪上条凳。
二拐斜眼看着哼哼唧唧的猪,从腰间抽出一尺二寸长的侵刀。举刀胸前,引来观众一阵惊叹,又在猪脖经上拍打几下,一来让血脉舒张,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二来让这畜生体会一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也好留下几句遗言。
待八戒心理生理都准备好了,大师低吟一个“走”字,寒光闪处,那宝刀已刺入脖颈。未等看客合上惊讶的嘴,大师又唱一个“接”字,新华递上脸盆,刀逆转,血涌如泉。刘娘的小宠物连一句戏文也没来得及喊出,便一名呜呼了。
看着鲜红的喷泉伴着蒸腾雾霭汩汩而下,老刘头不禁咂着牙花子拍手喝彩,一喝二拐的手艺,二也喝自家牲口的大义凛然。“到底是把势,就是利索。”
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老刘头这位“懂规矩”者一喝,二拐也来了精神。“要说这刀口……不能大,大了血喷,整的可那儿都是,灌不成血肠;也不能小,小了猪半天不死,哼哼唧唧的腻味。走刀不能太快,快了找不着‘寸’;也不能太慢,太慢口子就大了……”
“说得是,说得是。”老刘头一个劲地点头称是,递上第三根“带把的”。“她娘,赶紧收拾锅台。她娘……败家娘们,干啥去了?”
刘娘此时正对着墙上年画中的大胖娃娃祈祷,她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也不知什么仁义道德因果报应的玄妙。但她从心底不愿看到自己“打小看的”猪儿被屠杀,可为了过年,她又希望收获这蛋白质颇高的农作物。如此矛盾的心情从老刘头决定杀猪那时便久久萦绕在刘娘心头,她不知这忧愁从何而来,也许是转移了的意识让猪的身份产生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正如年画上抱着臃肿鲤鱼的白胖娃娃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民间娱乐范畴,进而升华为所谓的“民俗文化”了吧。
良久,老刘头一声吼打破了刘娘的哲学思考,漫天的神呀佛呀随着一道晴空霹雳变的无影无踪。刘娘回过神来,意识到那只是一头猪,还是一头猪。
“干啥呢,还不赶紧架锅台。”
“唉。”刘娘挤出笑容,默默走到外屋,猛一回首,似乎看到胖娃娃变成了一头站着雪白翅膀的猪,头上带着光圈,忽忽悠悠向上飞。
待老刘头再到当院,二拐已经开始吹猪了。屠户先用类似手铲的一把小刀弯开猪蹄,再把小指粗的一根铁筋探入,插在脂肪层和肌肉层之间,一下一下捅开个豁口。最后便是吹猪的看家本事,耍这把势得有相当的肺活量,没练过3、5年的断不能胜任。只见二拐深吸一口冷气,对准猪蹄上的豁口猛吹进去,大葱味的口气便合着屠夫的体温徐徐灌进死猪体内。新国新华哥俩用小木棍频频敲打猪身,让气脉疏通,均匀、流畅地走便猪身。师徒三人一吹二打,颇似当年某气功大师的运功走气。只不过气功大师耍的是把戏,终究要被揭穿,屠夫练的功夫,等食客吃到肉时自会称赞。
终于,吹猪大功告成。条凳上的死猪变成浑圆的一个球,看上去更加臃肿肥胖了。紧绷的皮肤带动了猪的表情,使之看上去更像是睡着了,而不是死了。滑稽的脸上似乎还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不知是在嘲笑自己的死亡还是人类的生存。二拐虽然是个老杀猪把势,可从未思考过死猪笑容之类的深刻问题。此时的他已经累得面红耳赤,蹲在地上不住喘气。
老刘头地上一碗开水,“歇会。”
“这算啥,不累。”二拐一边小心翼翼地吞下开水,一边指挥徒弟将气球猪抬进屋里。
中场休息之后,大师开始下半场的表演。浑圆的猪被架在锅台上,蒸汽朦胧蒸腾,二拐掏出3寸长的“刮子”逆着猪毛生长方向开始褪毛。锋利的刀片在圆滑的皮肤上游走,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清脆而悦耳。主人家一面的功劳就在这奏鸣曲中升腾飞扬。不多时,猪毛褪去,刚才还毛茸茸的八戒此时已做好了美容。浑圆还是浑圆,只是白净了许多,一身放着粉彩的皮肉被蒸汽熏的可人妩媚。摊在案板上,有如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稚嫩而多汁,让人禁不住喜从中来。
最后一道工序便是卸。二拐又摸了把小刀,将猪摆正,相它几相,刀下咽喉,直走屁眼,一条直线,白肉翻开,热气得腾,下水“呼”地冲出。“盆。”刘娘递上大盆,大师一刀一扒,肠肚进一盆;一刀一摘"灯笼挂"进一盆;一刀一捏,大肠头进一盆。心肝肠肺各归其位,只剩下一副肉墩墩的白净身躯。二拐再抽出长刀,手腕一旋,取了首级;换上小刀,手腕一拧,割下猪蹄。最后掏出小斧头,比上一比,顺着脊骨一斧一斧砍下去,将猪分成"半子"。两个“半子”挂上房梁,大功告成。
“二拐兄弟就是好把势,肉是肉膘是膘的。”老刘头再次称赞。
“猪好,把势就不能差。这肉他吃着也是那么回事儿呀。”
二人对着面前的一堆肉块欣赏了许久:是个拳头大小的猪蹄,两片红白相间的半子,三盆下水猪血,还有一个仍然微笑的猪头。被肢解的猪此时也算是寿终正寝,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分别”向主人家展示出它各个侧面的魅力。既有另人垂涎的“外表”,也颇具深刻的“内涵”。主人家一年的辛勤劳作和屠夫刚才的好一阵忙活此时得到了最大的回报,猪的死亡在每个人脸上都添了几分喜庆——刘娘也不例外。
刘娘正在进行一些屠户们不屑一顾的后续工作,搅拌凝固的猪血,清理大肠里的粪便,收拾散落四处的家什。琐碎的工作让她忘却了刚才的离别情怀,此时的猪在感情上也已经离开了,那份聊以寄托的爱此时变成了对食物的渴望,准确地说是对儿子们的渴望。
老刘头割了好大一块血脖塞给二拐,做为报酬,大师心满意足地带着徒弟们下班回家,心中盘算着明年的表演是否还能如此精彩,今晚是否应该大醉一场,徒弟们是否能孝敬几瓶烧刀子……诸如此类。
老夫妻俩忙活着处理猪的残肢断臂,或冰冻或火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每一块都是要按计划按步骤来食用的,分裂的猪昭示着即将团圆的家,儿子们回来是要吃肉的,亲戚们串门是要招待的。过年的喜庆也就随着这生命的流逝步步迫近。
猪死了,人活着,老刘头赶集时还会再买一头猪仔,为了明年的喜庆,也为了明年的寄托。
猪吃了,人乐了,刘娘还会一如既往地照顾出另一头膘肥体壮的猪,还会寄托一些感情,还会有一丝酸楚。
大家都很开心,连死去的猪也仍然挂着它人生哲学赠与的微笑。 快过年了,杀头猪给大家打牙祭……
这个猪不是别的猪,猪和猪还是有区别的,杀和杀也是有区别的,写这个只是为了怀念某些离我们远去的东西。
细细咀嚼,您会发现人的哲学中也有猪的精神,而人类技艺与猪哲学的混合便会衍生出一些让我们有感与怀而有不可言状的东西来。
例如……杀猪 数日未见布朗兄了,不知是否无恙? 进来笔锋颇为不顺,只好借酒引文,不料酒是饮了不少,文却只字未出,无奈无奈……
回复 #5 旱地忽律布朗 的帖子
呵呵,所谓抽到断水水更流,稍事休息几天无妨。希望不要给布朗兄带来太大压力为要。 谢谢分享! 嗯,人生哲学………… 我嗅到了熟悉的东北味 我都有点想写了。 布郎还在哪里写文,好久不见屠龙者了,哎,一声叹息。 看了筷子一说于是翻阅兄才其它作品,杀猪一篇尤其生动!诉事文体追求的也就是再现此事的情景以及结合当事人的反应、心理活动,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就是写作人的诚意和经验了。不过实在不能料到如此浑然天成的文字出自蜥蜴特之手,我想怎么也应该是蛮牛特这样的人物,佩服,还希望前辈回来,继续如此真实和真诚的文字。
页:
[1]